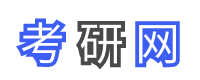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期刊
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
申丹教授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雅讲席教授、人文学部主任,受聘为美国Narrative杂志顾问、Style杂志顾问、英国Language and Literature杂志编委、英美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顾问编委,连年上榜Elsevier在国际上高被引的中国学者榜单。研究方向:叙事理论与小说阐释、文体学、翻译学。
提要:
本文接合笔者自己近几年在国际学术前沿探索的经历, 从四个方面谈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1) 总结探索, 分类评析跨学科研究的新发展; (2) 廓清画面, 清理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混乱; (3) 透过现象看本质, 化对立为互补; (4) 利用跨学科优势, 做出创新性的分析。
跨学科研究;自主创新;分类评析;化对立为互补;综合分析;
文献来源:申丹.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J].中国外语,2007,No.15(1):13-18.
0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 随着跟国际学术界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和接轨, 我国的外语科研从强调引进介绍逐渐转向强调创新和发展。2001年, 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召开的首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 将“外语科研创新”明确作为一个中心议题, 我当时为那届沙龙写了一篇文章, 从以下四个方面谈了外语科研创新的问题: (1) 不迷信广为接受的权威观点; (2) 从反面寻找突破口; (3) 根据中国文本的实际情况修正所借鉴的外国理论模式; (4) 通过跨学科研究达到创新与超越 (申丹, 2001) 。本文将结合近几年笔者自己的科研经历, 从新的角度谈外语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的关系, 主要涉及以下四个方面: (1) 总结探索、分类评析跨学科研究的新发展; (2) 廓清画面, 清理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混乱; (3) 透过现象看本质, 化对立为互补; (4) 利用跨学科优势, 做出创新性的分析。
02
总结探索、分类评析跨学科研究的新发展
文体学与叙事学 (或叙述学) 都属于生命力较强的交叉学科。20世纪90年代以来, 英国成为国际文体学研究的中心, 而美国也取代法国, 成为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中心。我一直在关注这两个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的情况, 发现叙事学家很少关注文体学, 但越来越多的西方文体学家注重借鉴叙事学。我对这些跨学科论著进行了仔细考察, 发现文体学借鉴叙事学的方式可以分为三类: (1) 温和的方式, (2) 激进的方式, (3) 平行的方式。西方文体学家对叙事学的借鉴大多采用“温和的”方式, 即采用叙事学的概念或模式作为文体分析的框架。文体学对叙事学的“温和”借鉴是克服文体学之局限性的一种较好的做法, 但容易受到文体分析本身的限制。文体学聚焦于语言特征, 即便借鉴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 也往往只起辅助作用, 为语言分析铺路搭桥, 这必然导致对一些重要结构技巧的忽略。
与“温和”的方式相对照, 有的西方文体学家采用了较为“激进”的方式来“吸纳”叙事学。保罗·辛普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2004年面世的《文体学》这部新作中, 辛普森采用了“叙事文体学”这一名称来同时涵盖对语言特征和叙事结构的研究。这是克服文体学之局限性的一种大胆创举, 但出现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 在理论界定中, 辛普森有时将叙事学的概念 (如“故事情节”与“话语”之分) 视为文体学的概念 (Simpson, 2004:20)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文体学自身的特性。其次, 虽然文体学和叙事学都声称采用语言学模式来研究作品, 但叙事学往往只是比喻性地采用语言学, 因此并未受到语言学对文字关注的限制, 其分析对象包括各种非文字叙事媒介。辛普森按叙事学的做法, 将各种叙事媒介均视为“叙事文体学”的分析对象, 包括电影、芭蕾舞、音乐剧或连环漫画 (Simpson, 2004:20-1) 。若这样拓展, 文体学就会失去其自身的性质。真正采用语言学模式的文体学只能研究语言媒介。以往文体学家认为作品中重要的就是语言, 但身处新世纪的辛普森已认识到文体学仅关注语言的局限性, 因此有意识地借鉴叙事学。然而, 也许是“本位主义作祟”, 他不是强调文体学与叙事学的相互结合, 而是试图通过拓展文体学来“吞并”叙事学。其实, 无论如何拓展“语言系统”, 都难以涵盖“芭蕾舞、音乐剧或连环漫画”。
此外, 就文字性叙事作品本身而言, 辛普森在探讨“话语”表达这一层次时, 有时也将语言结构 (文体学的分析对象) 和叙事结构 (叙事学的关注对象) 相提并论。他举了下面这一实例来说明叙事学所关心的“话语”表达层对事件顺序的安排:“约翰手中的盘子掉地, 珍妮特突然大笑”。这两个小句的顺序决定了两点: (1) 约翰的事故发生在珍妮特的反应之前; (2) 约翰的事故引起了珍妮特的反应。倘若颠倒这两个小句的顺序 (珍妮特突然大笑, 约翰手中的盘子掉地) , 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阐释:珍妮特的笑发生在约翰的事故之前, 而且是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辛普森用这样的例子来说明对事件的“倒叙”和“预叙” (Simpson, 2004:18-20) 。在我看来, 文体学家所关心的语言层面上的句法顺序与叙事学家所关注的“倒叙”和“预叙”等结构顺序只是表面相似, 实际上迥然相异。“倒叙”和“预叙”等结构顺序仅仅作用于形式层面, 譬如, 究竟是先叙述“他今天的成功”再叙述“他过去的创业”, 还是按正常时间顺序来讲述, 都不会改变事件的因果关系和时间进程, 而只会在修辞效果上有所不同。这与辛普森所举的例子形成了截然对照。此外, 句法顺序需要符合事件的实际顺序。就辛普森所举的例子而言, 如果是约翰的失手引起了珍妮特的大笑, 就不能颠倒这两个小句的顺序 (除非另加词语对因果关系予以说明) 。与此相对照, 在超出语言的“话语”表达层面, 不仅可以用“倒叙”、“预叙”等来打破事件的自然顺序, 而且这些手法具有艺术价值。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将文体学关心的句法顺序和叙事学关心的“话语”表达顺序视为同一种类。
正如“叙事文体学”这一名称所体现的, 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在西方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发展趋势。这固然有利于对叙事作品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但若处理不当, 则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文体学和叙事学各有其关注对象和分析原则。既然文体学关心的是“语言”, 就难以用任何名义的文体学来涵盖或吞并叙事学。在实际分析中, 若想克服两者各自的局限性, 不妨将两种方法交织贯通, 综合采纳。
下面让我们看看“并行的方式”。为了克服文体学和叙事学各自的局限性, 有的文体学家不仅两方面著书, 而且也两方面开课。迈克·图伦 (Michael Toolan) 就是其中之一。他身为著名文体学家, 却也写出了叙事学方面的书 (Toolan, 2001) 。有的文体学家在同一论著中, 既进行叙事学分析, 又进行文体学分析。譬如, 米克·肖特 (Mick Short) 在探讨一部小说时, 先专辟一节分析作品的结构技巧, 然后再聚焦于语言特征, 旨在说明作品的“叙事学创新”和“语言创新”如何交互作用 (Short, 1999) 。凯蒂·威尔士在她主编的《文体学辞典》 (Wales, 2001) 中, 也收入了不少叙事学的概念, 有的是独立词条, 有的则与文体学的概念一起出现在同一词条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两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相互之间的互补性。与“激进的”方法形成对照, “并行的”方法没有试图用文体学来“吞并”叙事学, 而是保持了两者之间清晰的界限。但采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往往未注意说明文体学和叙事学各自的局限性和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而是让它们分别以独立而全面的面目出现。图伦在1998年出版的《文学中的语言:文体学导论》一书中对文体学的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是:
文体学研究的是文学中的语言……至关重要的是, 文体学研究的是出色的技巧。(Toolan, 1998:viii-ix)
图伦在2001年再版的《叙事:批评性的语言学导论》一书中对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所下的定义则是:
[叙述学的]“话语”几乎涵盖了作者在表达故事内容时以不同的方式所采用的所有技巧。(Toolan, 2001:11)
从上面这些定义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等式:
文体=语言=技巧=话语
但只要考察一下“文体”与“话语”的实际所指, 就会发现难以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譬如, 文体学和叙事学都关注作品中的“节奏”。文体学家关注的“节奏”指的是文字的节奏, 其决定因素包括韵律、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之间的交替、标点符号、词语或句子的长短等等。与此相对照, 在叙事学研究中, “节奏”指的是叙述运动的节奏:对事件究竟是简要概述 (譬如用一句话概括10年的经历) 还是详细叙述 (譬如用10页纸的场景展示一小时之内发生的事) , 究竟是略去不提还是像电影慢镜头似地缓慢描述等等。第一种“节奏”是对语言的选择, 第二种“节奏”则是对叙述方式的选择。在我看来, 鉴于目前的学科分野, 无论是在文体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论著和教材中, 都有必要明确说明小说的艺术形式包含文字技巧和结构技巧这两个不同层面, 文体学聚焦于前者, 叙事学则聚焦于后者。威尔士在《文体学辞典》中将“文体”界定为“对形式的选择”或“写作或口语中有特色的表达方式” (Wales, 2001:158, 371) 。这是文体学界对“文体”通常加以的界定。这种笼统的界定掩盖了“文体”和“话语”之间的差别, 很容易造成对小说艺术形式的片面看法。我们不妨将之改为:“文体”是“对语言形式的选择”, 是“写作或口语中有特色的文字表达方式”。至于叙事学的“话语”, 我们可以沿用以往的定义, 如“表达故事的方式”, 但必须说明, 叙事学在研究“话语”时, 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文体”这一层次, 而“文体”也是“表达故事的方式”的重要组成成分。
美国的《文体》 (Style) 杂志最近刚刚面世的第39卷第4期首篇刊发了我的论文《文体学家是如何借鉴叙事学的:不同方式, 长处和短处》 (Shen, 2005a) , 在这篇论文中, 我较为详尽地分析了文体学借鉴叙事学的不同方式, 分析了每一种方式的长处和短处, 并对今后的学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总之, 我们可以更多地关注有互补关系的学科之间出现的跨学科借鉴的情况, 适时对不同借鉴方式加以分类, 分析探讨每一种方式的所长所短, 这有利于更好地看清两个学科各自的特性和相互之间的互补性, 还有可能对下一步的学科发展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03
廓清画面, 清理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混乱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读者认知在西方越来越受到重视, 诞生了一些与认知科学或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 如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等。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之时, 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 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 但更为重要的是, 它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我认为, 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 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是“叙事语境”, 二是“社会历史语境”。“社会历史语境”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叙事语境”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 (“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 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 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 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 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或认知框架。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 这种读者的阐释受到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和个人经历、身份的影响。我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个体读者之间的差异, 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享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若仔细考察, 可以发现认知叙事学中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 涉及多种不同的研究对象 (申丹等, 2006:309;Shen, 2005b:156-7) , 但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都聚焦于读者对于 (某文类) 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 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和“规约性叙事认知者”。也就是说, 当认知叙事学家研究读者对某部作品的认知过程时, 他们往往是将之当作实例来说明叙事认知的共性。因此,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 切忌望文生义, 一看到“语境”、“解读”等词语, 就联想到不同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 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 聚焦于“叙事”或“某一类型的叙事”之认知规约, 往往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 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就创作而言, 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 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 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 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 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 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 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 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我在美国的《叙事理论杂志》 (JNT: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第35卷第2期上首篇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Shen, 2005b:155-61) , 梳理了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不同关系, 清理了相关混乱。
跨学科研究往往能丰富研究方法, 开拓新的研究角度, 但也常常带来新的混乱。1999年, 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 (Kearns, 1999) , 该书旨在将修辞学的方法与叙事学的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而这种结合是以言语行为理论为根基的。由于卡恩斯将言语行为理论作为基础, 因此在修辞性叙事理论中很有特色, 但书中的逻辑混乱恐怕也是最多的。卡恩斯的模式聚焦于叙事的三个方面:语境、基本规约和话语层次。我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上发表了一篇两万字的长文, 集中探讨了这三个方面的实质性内涵, 清理了有关混乱。我在美国的《叙事理论杂志》上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也辟专节探讨了卡恩斯的研究中的种种混乱 (Shen, 2005b:161-4) 。跨学科研究中经常出现一些混乱, 为我们自主创新的研究提供了一定余地。这也是我们可以进一步关注的一个方面。
04
透过现象看本质, 化对立为互补
美国的《叙事理论杂志》第35卷第2期首篇发表了我的《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为何相互需要》一文 (Shen, 2005b) 。这是一篇反潮流的论文, 西方学界普遍认为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学之间是一种对立和取代的关系, 而这篇论文则旨在说明在过去的20年中, 语境叙事学和形式叙事诗学之间是一种互为滋养、相互促进的关系。该文指出, 在语境主义研究的范围内外, 存在一种未被承认的三重对话关系: (1) 新的形式理论和语境批评之间的互利关系; (2) 关注语境的学者对形式叙事诗学的新贡献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互利关系; (3) 经典叙事诗学与语境化叙事批评之间的互利关系。我之所以能看清这一点, 跟我国的学术氛围密切相关。西方学界20世纪上中叶一直在搞形式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味从事政治文化批评, 排斥形式审美批评。而中国学界则是在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之后, 才开展形式审美研究的, 对形式结构研究有较为客观的看法。在这一氛围中, 我对西方排斥经典叙事学的做法进行了认真考察, 发现西方学界没有看清叙事诗学作为一种“文本语法”和叙事批评作为一种“文化产物之解读”之间的不同, 也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近年来, 我跟美国的一些著名叙事理论家进行了交流, 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 看到经典叙事诗学没有过时, 看到经典叙事诗学和语境叙事学之间实际上是互利互补而不是对立和取代的关系。在此我有两点体会: (1) 一种批评理论或方法究竟是否“合法”与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在西方形式主义文评占据了多年主导地位以后, 形式结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看成为维护统治意识服务的保守方法;而中国经历了长期政治批评之后, 形式结构研究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思想的解放。尽管中国学者近年来越来越关注社会历史语境, 但很少有中国学者把文学批评视为政治工具, 从政治上反对形式审美研究, 这与西方学界形成了鲜明对照。(2) 应充分利用中国文化特有的学术氛围, 来反思西方的学术现象, 尤其是一些时髦、激进的学术现象, 避免被其所误导。同时应利用国际交流, 促使西方学者改变看法。
在西方学界, 还存在一种明显的两派对立, 即从结构主义发展而来的叙事学与解构主义的对立。美国著名解构主义学者希利斯·米勒 (Hillis Miller) 1998年出版了《解读叙事》一书, 他称该书为一部“反叙事学” (ananarratology) 的著作 (Miller, 1998:49) 。但无论米勒如何标榜自己“反”叙事学, 我发现他的实际分析常常与叙事学的分析构成一种互补关系。且以叙事作品的开头为例。一般认为传统情节具有开头、中间发展、结尾这样的完整性。叙事学研究十分关注传统情节。诚然, 很多现代和后现代作品以各种方式有意打破了情节的完整性, 但叙事学家只是将之视为对传统情节的偏离。在话语层次上, 很多叙事学家关注的是作者如何打破自然时序, 但这种探讨也是建立在情节统一性之上的:只有当故事具有开头时, 才会出现“从中间开始的叙述”。同样, 只有当故事具有所谓“封闭式”结局时, 才会出现“开放式”的结尾。在《解读叙事》中, 米勒提出开头涉及一个悖论:既然是开头, 就必须有当时在场和事先存在的事件, 由其构成故事生成的源泉, 为故事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事先存在的基础本身需要先前的基础作为依托。倘若小说家采取“从中间开始叙述”这一传统的权宜之计, 譬如突如其来地描写一个人物把另一个人物扔到了窗外, 他迟早需要解释是谁扔的谁, 为何这么做。而这种解释会导致一步步顺着叙事线条回溯, 无穷无尽的回退 (Miller, 1998:57-60) 。米勒对于叙事线条不可能有开头的论证令人深受启发, 但这一论证以不考虑文本的疆界为前提。我认为, 这是一种宏观的观察角度。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一部剧或一个文本 (的封面) 构成了一种疆界。若以《俄狄浦斯王》这部剧为单位来考虑, 特尔斐神谕和襁褓中的俄狄浦斯被扔进山里就构成俄狄浦斯弑父娶母这一事件的开头。但倘若打破文本的疆界, 转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那么“襁褓中的俄狄浦斯被扔进山里”就不成其为开头, 因为可以永无止境地顺着叙事线条回溯尚未叙述的过去, 譬如俄狄浦斯父母的恋爱、结婚──其父母的成长──其 (外) 祖父母的恋爱、结婚──如此等等, 永无止境。由此看来, 常规概念上作品的开头是在叙事惯例的基础上, 作者的创作与文本的疆界共同作用的产物。
承认文本的疆界就是承认叙事规约, 打破文本的疆界就是颠覆叙事规约, 两者在根本立场上完全对立, 但由于两者涉及了观察范围从微观到宏观的变化, 因此又在实际分析中, 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米勒在解构开头和结尾的同时, 又对《项狄传》作了这样的评价:“像《项狄传》这样的小说打破了戏剧性统一的规则。它缺乏亚里士多德那种有开头、中部和结尾的摹仿上的统一性。” (Miller, 1998:74) 显然, 米勒在此采用的是以单一文本为单位的微观视角。有了这种视角, 我们就可以比较在文本的疆界之内呈统一性的文本和《项狄传》这种打破戏剧性统一规则的文本。若一味强调不存在开头和结尾, 不存在任何统一性, 就难以对不同种类的文本进行比较和评论。值得强调的是, 叙事学的微观视角和解构主义的宏观视角互为补充。我在这方面化对立为互补的一篇论文于2005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挑战阅读》一书中面世 (Shen, 2005c) 。
然而, 我们要避免盲目地化解客观存在的对立。在《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 英国学者马克·柯里 (Mark Currie) 也试图化解解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叙事学之间的对立。柯里对库恩 (Kuhn) 将解构主义视为对结构主义的线性取代提出了挑战, 他认为, 将解构主义这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方法视作被叙事学激活或充实的方法可能会更现实些 (Currie, 1998:9-10) 。顺着这一思路, 解构主义被当作是叙事学的一种新形式, 也就是, “后结构主义叙事学”, 于是, 叙事学的发展就成了“从演绎科学到对语言知识的归纳性解构”的演变 (Currie, 1998:46-47) 。但把解构主义本身视为叙事学的新发展则忽略了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叙事学有赖于叙事规约并在后者的范围内运作, 而解构主义则旨在彻底推翻叙事规约。
就哲学立场而言, 一般认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的关系性质的强调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了支持。但事实上,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 表面上存在着两股相互对抗的力量。其中一股特别重视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将语言定义为“一个符号体系, 其中惟一本质的东西是意义和声音—意象的结合, 而且符号的这两个部分都是心理层面的” (Saussure, 1960:15) 。另一股力量只是把语言视为一个由“差异”构成的体系, “更重要的是:差异通常意味着存在实在的词语, 在这些词语之间产生差异, 但语言中只存在差异, 不存在实在的词语。” (Saussure, 1960:120) 的确, 西方语言通常由完全任意的符号构成, 因此不存在实在的词语。但我们必须意识到, 差异本身并不能产生意义。在英语里, “sun” (/s∧n/) 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符号, 不仅仅是因为它与其他符号在声音或“声音—意象”上的差异, 而且还出于声音—意象“sun”与所指概念之间约定俗成的关联。比如说, 尽管以下的声音—意象“lun” (/l∧n/) , “sul” (/s∧l/) 和“qun” (/kw∧n/) 中的每一个都能与其他两个区分开来, 但没有一个能成为英语中的语言符号, 这是因为缺乏常规的“意义和声音—意象之间的关联”。在《立场》 (Positions) 及其他著述中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进行评价时, 德里达仅仅关注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作为能指差异体系的强调, 而忽略了索绪尔对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强调。我们知道,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区分了语言形成过程中的三种任意关系: (1) 能指差异的任意体系; (2) 所指差异的任意体系; (3) 特定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联。因为德里达忽略了特定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联, 所以, 能指和所指之间就失去了联系, 理由很简单:“能指和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关联”是联系能指和所指的惟一且必不可少的纽带。没有这种约定俗成的关联, 语言就成了能指自身的一种游戏, 它无法与任何所指发生联系, 意义自然也就变得无法确定。也就是说, 德里达和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是直接对立的, 而并不是像学界过去几十年所一直认为的那样,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提供了支持。我的这一反潮流的观点也新近发表于美国《美国叙事理论》杂志 (Shen, 2005b:144-5) 。
05
利用跨学科优势, 做出创新性分析
跨学科研究不能局限于理论探讨, 也应该关注实际分析。我曾经把文体学引入翻译批评, 对理解译本起了很好的深化和促进作用, 同时又通过原文和一个或多个译本的对照, 为文体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分析素材, 有多篇研究成果在欧美重要国际刊物上发表。近年来, 我尤为注重通过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的方法结合, 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做出新的阐释。譬如, 2005年, 国际上第一部《叙事理论指南》先后在英美和加拿大面世, 其中有我应邀撰写的一章, 题为“叙事学和文体学能相互做什么” (Shen, 2005d) , 在该文中, 我不仅从理论上论述了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互补关系, 而且将两个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 对海明威的一个短篇小说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以前未被关注的多重深层象征意义。又如, 欧洲的《英语研究》杂志2006年第二期登载了我的一篇论文, 题为“颠覆表面意义, 使反讽双重化:曼斯菲尔德《启示》和其他作品中的潜藏文本” (Shen, 2006) , 这篇论文综合采用文体学的语言分析和叙事学的结构分析的方法, 并且将内在批评与外在批评、作品分析与互文探讨相结合, 利用综合优势, 挖掘了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深层意义或暗含意义, 挑战了西方学界以往的阐释。
06
结语
总而言之, 跨学科研究与自主创新关系密切。跨学科研究既可为我们的自主创新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又可成为我们自主创新的研究对象, 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余地, 让我们争取改变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 或为学科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希望我们今后更多地关注跨学科研究这一领域, 希望能看到更多跨学科的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询知网或者《中国外语》2007年第1期纸质期刊了解详情。
转自:语言治理研究
【特别声明】本公众平台除特别注明原创或授权转载外,其他文章均为转载,版权归原作者或平台所有,出于传递信息之目的,并没有任何商业目的。本公号尊重知识产权,如无意中侵犯了您的权益,请及时联系后台,本公号将及时删除。
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期刊)